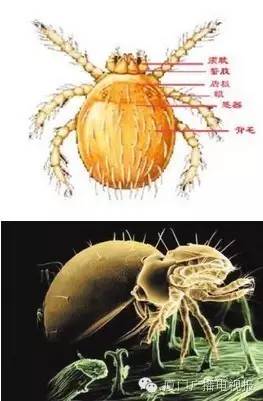不过村名确实和清初驻扎满兵有关,老辈人说当时还筑有土城呢,地势是整个村最高的地方,就叫满洲城里;后来满兵撤离,赵姓入住了。

(网络配图)
所谓城里,其实只有个大台门,门口有两面石鼓守护,门外就是田畈,门里一户户分门别院。我外婆家就坐落于满洲城里,外婆家的别院称作“满洲城里小书房”,听着挺有点书香门第的味道。
我是在外婆家出生的,那年父亲还在部队。六岁时,父亲从部队回来,我离开满洲回自己村上学,一呆六年。依稀记得家中出现什么变故,父亲带我们全家又搬迁回到了外婆家,我幼小的心灵中,却有“回家了”的安定感。
我是外来人口,不过也没有被本地人排斥。相反,左邻右舍的叔伯姨母们都对我疼爱有加,串门进哪一家,都是有什么好吃的就往我兜里塞,就是曾经的小玩伴,邻家哥哥姐姐,对我都是有种失而复得的欢迎。对满洲,我有极浓郁的感情。
我们满洲村,被一条汽车路由东向西劈开。碎石子铺的车路,晴天连自行车踏过都会有尘土扬起。我家在马路北边,屋后门出去是草塔老街,这是草塔最早的市集所在地。

(草塔老街一景)
一大早,豆浆油条、肉馒头、馄饨,香气直钻眠床里的“贪吃妞”。于是,我随随便便梳洗好,就急匆匆领上一块钱背上书包去老街吃早饭。我还记得母亲的唠叨:“投胎到街头市面要修三生呢,哪个娃能有你这样好口福,早饭变着花样吃。”
现在,老街变样了,摊贩不摆大街上了,下雨天,再也感受不到躲塑料雨布下怕雨布兜住的水泄下来战战兢兢的感觉了。草塔名小吃年糕糳也已经用上了烤箱,不再是炭火炉子的焦香了。
路南边是田畈,叫门前畈。我一半童年时间是在这田畈里撒野。汽车路边有岔路笔直通到田畈尽头,尽头的溪滩叫石钵潭。溪埂边有孤孤零零、矮矮黑黑的一层小楼,蜷缩在几棵老梧桐树下。

(草塔老街一景)
晚上,从我家的窗户可以遥望到那隐约的煤油灯火,总是感觉那屋子笼罩着神秘与恐怖。小伙伴们每每到屋门口都会不由自主奔跑起来。石钵潭是个芦苇丛丛的“儿童乐园”,溪水清澈,滩里的鹅卵石隙间小鱼、小虾米成群结队,孩子们闲暇时都不用通气便汇聚到此。滩上有野生胡萝卜,拔出来用溪水洗洗就可以直接入口。特别是秋季,随便钻进谁家地里刨几个番薯,溪边找几块大卵石一搭,弄点干稻草干树枝烤番薯。

(网络配图)
在这个乐园,我储存了整个从等着吃番薯的“小跟班”到亲自烤番薯给我的“小跟班”吃的成长记忆。我难以忘记石钵潭秋季美景。芦苇被舞弄得漫天飞絮,我们撒欢地飞奔,留下银铃般笑声。

(网络配图)
还有那成片成片金黄的稻田,像皇宫里的金碧,辉煌得不可一世。而已经收割的稻草堆,是小伙伴们捉迷藏的好去处。那时,你会看到有一个女娃娃,扎着两支乌鸦辫子,与稻草人说话,那个人就是我喽。

(网络配图)
满洲就在田畈边上。寒假里,孩子们最盼望的是清晨起床能看到遍野的白茫茫,收割掉稻子的稻田被雪铺上像铺着白色皮草一样诱人,简直可以上去打个滚。
听到春雷发声,我就去门前畈挑野菜了,荠菜被雪覆盖以后,早就悄悄展开,天一放晴,乍暖还寒的时光,就该出手了。这时候的荠菜像向日葵一样圆圆的脸盘,平摊在田头。“看,我这个有芝麻饼那么大呢。”找到特壮的就会惊喜喊出来。于是,大家蜂拥而来,集中在一处找寻。

(网络配图)
再暖和一点,马兰头自然又可以下手了。春季里,退休的老外公下酒菜,会常常有香干马兰头“搭色”了。夏季是男孩子最爱的吧,因为我不会游泳,只有岸边上干巴巴坐等,等他们玩爽快了,提个簸箕带上我去边上溪坑里围堵抓鱼,或翻小石头缝里的咪咪螃蟹。想象得出那个留着哈喇子,等着老外婆炸面包猫鱼、狗爬蟹的小女孩不?

(网络配图)
青春年代,石钵潭边成了我静思的最佳去处,捧上一本书,往坡地的草上一躺,叼一根狗尾巴草,任思绪天马行空。偶尔想想初恋的男孩,憧憬一下未来。想到某次听家里大人在闲聊,隔壁姐姐某夜幽会在田畈里跟男朋友亲嘴,被人电筒照到抓了个正着。于是,这片田畈,又多出了一份爱情的浪漫与缠绵。
如今,溪滩变了样,芦苇荡没有了,砌起了整齐规范的柏油堤埂骑行道。但是那份悠然与浪漫犹存。走路的走路,钓鱼的钓鱼,摸螺蛳的摸螺蛳,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还有约上三五好友席地而坐喝点啤酒侃大山。夜色笼罩,我回望稻田那边满洲村渐次稀疏了灯光,而袜业作坊嘚嘚的机器声,押着星光闪烁的韵脚,不知从何处持续不断地传来。
(杨赪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