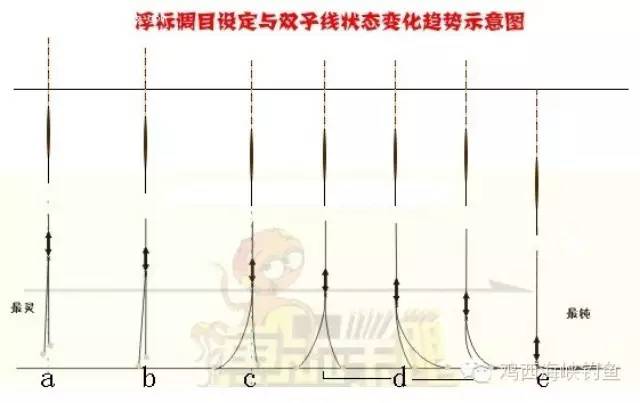建议
早读时间:7:00至10:00
晚读时间:19:00至22:00
来自:《瓦尔登湖》第9-10章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
美国作家、思想家、自然主义者,19世纪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梭罗的著作都是根据他在大自然中的体验写成。发表了对自然、人生和文艺问题的见解。在他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
梭罗是生活的智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孤独者。因为一个半世纪前,人类对于技术的崇拜与痴迷是不允许任何人来亵渎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瓦尔登湖》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梭罗的声誉也与日俱增,被誉为美国生态运动的思想先驱,他在书中所阐述的许多思想,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第9-10章
有时,对人类社会及其言谈扯淡,对所有村中的友人们又都厌倦了,我便向西而漫游,越过了惯常起居的那些地方,跑到这乡镇的更无人迹的区域,来到“新的森林和新的牧场”上;或当夕阳西沉时,到美港山上,大嚼其越橘和浆果,再把它们拣拾起来,以备几天内的食用。
水果可是不肯把它的色、香、味给购买它的人去享受的,也不肯给予为了出卖它而栽培它的商人去享受的。要享受那种色、香、味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很少人采用这个办法。如果你要知道越橘的色、香、味,你得请问牧童和鹧鸪。从来不采越橘的人,以为已经尝全了它的色、香、味,这是一个庸俗的谬见。从来没有一只越橘到过波士顿,它们虽然在波士顿的三座山上长满了,却没有进过城。水果的美味和它那本质的部分,在装上了车子运往市场去的时候,跟它的鲜丽一起给磨损了,它变成了仅仅是食品。只要永恒的正义还在统治宇宙,没有一只纯真的越橘能够从城外的山上运到城里来的。在我干完了一天的锄地工作之后,偶尔我来到一个不耐烦的侣伴跟前,他从早晨起就在湖上钓鱼了,静静的,一动不动的,像一只鸭子,或一张漂浮的落叶,沉思着他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而在我来到的时候,大致他已自认为是属于修道院僧中的古老派别了。
有一个老年人,是个好渔夫,尤精于各种木工,他很高兴把我的屋子看作是为便利渔民而建筑的屋子,他坐在我的屋门口整理钓丝,我也同样高兴。我们偶尔一起泛舟湖上,他在船的这一头,我在船的另一头;我们并没有交换了多少话,因为他近年来耳朵聋了,偶尔他哼起一首圣诗来,这和我的哲学异常地和谐。我们的神交实在全部都是和谐的,回想起来真是美妙,比我们的谈话要有意思得多,我常是这样的,当找不到人谈话了,就用桨敲打我的船舷,寻求回声,使周围的森林被激起了一圈圈扩展着的声浪,像动物园中那管理群兽的人激动了兽群那样,每一个山林和青翠的峡谷最后都发出了咆哮之声。在温和的黄昏中,我常坐在船里弄笛,看到鲈鱼游泳在我的四周,好似我的笛音迷住了它们一样,而月光旅行在肋骨似的水波上,那上面还零乱地散布着破碎的森林。
很早以前,我一次次探险似的来到这个湖上,在一些夏天的黑夜里,跟一个同伴一起来;在水边生了一堆火,吸引鱼群,我们又在钓丝钩上放了虫子作鱼饵钓起了一条条鳘鱼;这样我们一直搞到夜深以后,才把火棒高高地抛掷到空中,它们像流星烟火一样,从空中落进湖里发出一些响亮的咝声,便熄灭了,于是我们就突然在完全的黑暗之中摸索。我用口哨吹着歌,穿过黑暗,又上路口到人类的集名处。
可是现在我已经在湖岸上有了自己的家。有时,在村中一个客厅里待到他们一家子都要休息时,我就回到了森林里;那时,多少是为了明天的伙食,我把子夜的时辰消耗在月光之下的垂钓之上,坐在一条船里,听枭鸟和狐狸唱它们的小夜曲,时时我还听到附近的不知名的鸟雀发出尖厉的啸声。这一些经验对我是很值得回忆和很宝贵的,在水深四十英尺的地方抛了锚,离岸约二三杆之远,有时大约有几千条小鲈鱼和银鱼围绕着我,它们的尾巴给月光下的水面点出了无数的水涡;用了一根细长的麻绳,我和生活在四十英尺深的水底的一些神秘的夜间的鱼打交道了,有时我拖着长六十英尺的钓丝,听凭柔和的夜风把我的船儿在湖上漂荡,我时不时地感到了微弱的震动,说明有一个生命在钓丝的那一端徘徊,却又愚蠢地不能确定它对这盲目撞上的东西怎样办,还没有完全下决心呢。到后来,你一手又一手,慢慢地拉起钓丝,而一些长角的鳘鱼一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边扭动着身子,给拉到了空中。特别在黑暗的夜间,当你的思想驰骋在广大宇宙的主题上的时候,而你却感到这微弱的震动,打断了你的梦想,又把你和大自然联结了起来,这是很奇怪的。我仿佛会接着把钓丝往上甩,甩到天空里去,正如我同时把钓丝垂入这密度未必更大的水的元素中去的情况一样。
这样我像是用一只钓钩而捉住了两条鱼。瓦尔登的风景是卑微的,虽然很美,却并不是宏伟的,不常去游玩的人,不住在它岸边的人未必能被它吸引住:但是这一个湖以深邃和清澈著称,值得给予突出的描写。这是一个明亮的深绿色的湖,半英里长,圆周约一英里又四分之三,面积约六十一英亩半;它是松树和橡树林中央的岁月悠久的老湖,除了雨和蒸发之外,还没有别的来龙去脉可寻。
四周的山峰突然地从水上升起,到四十至八十英尺的高度,但在东南面高到一百英尺,而东边更高到一百五十英尺,其距离湖岸,不过四分之一英里及三分之一英里。山上全部都是森林。所有我们康科德地方的水波,至少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站在远处望见的,另一种,更接近本来的颜色,是站在近处看见的。第一种更多地靠的是光,根据天色变化。在天气好的夏季里,从稍远的地方望去,它呈现了蔚蓝颜色,特别在水波荡漾的时候,但从很远的地方望去,却是一片深蓝。在风暴的天气下,有时它呈现出深石板色。
海水的颜色则不然,据说它这天是蓝色的,另一天却又是绿色了,尽管天气连些微的可感知的变化也没有。我们这里的水系中,我看到当白雪覆盖这一片风景时,水和冰几乎都是草绿色的。有人认为,蓝色.乃是纯洁的水的颜色,无论那是流动的水“或凝结的水”。可是,直接从一条船上俯看近处湖水,它又有着非常之不同的色彩。甚至从同一个观察点,看瓦尔登是这会儿蓝,那忽儿绿。置身于天地之间,它分担了这两者的色素。从山顶上看,它反映天空的颜色,可是走近了看,在你能看到近岸的细砂的地方,水色先是黄澄澄的,然后是淡绿色的了,然后逐渐地加深起来,直到水波一律地呈现了全湖一致的深绿色。
却在有些时候的光线下,便是从一个山顶望去,靠近湖岸的水色也是碧绿得异常生动的。有人说,这是绿原的反映;可是在铁路轨道这儿的黄沙地带的衬托下,也同样是碧绿的,而且,在春天,树叶还没有长大,这也许是太空中的蔚蓝,调和了黄沙以后形成的一个单纯的效果。这是它的虹色彩圈的色素。也是在这一个地方,春天一来,冰块给水底反射上来的太阳的热量,也给土地中传播的太阳的热量溶解了,这里首先溶解成一条狭窄的运河的样子,而中间还是冻冰。在晴朗的气候中,像我们其余的水波,激湍地流动时,波平面是在九十度的直角度里反映了天空的,或者因为太光亮了,从较远处望去,它比天空更蓝些;而在这种时候,泛舟湖上,四处眺望倒影,我发现了一种无可比拟、不能描述的淡蓝色,像浸水的或变色的丝绸,还像青锋宝剑,比之天空还更接近天蓝色,它和那波光的另一面原来的深绿色轮番地闪现,那深绿色与之相比便似乎很混浊了。
这是一个玻璃似的带绿色的蓝色,照我所能记忆的,它仿佛是冬天里,日落以前,西方乌云中露出的一角晴天。可是你举起一玻璃杯水,放在空中看,它却毫无颜色,如同装了同样数量的一杯空气一样。众所周知,一大块厚玻璃板便呈现了微绿的颜色,据制造玻璃的人说,那是“体积”的关系,同样的玻璃,少了就不会有颜色了。应该有多少的水量才能泛出这样的绿色呢,我从来都无法证明。一个直接朝下望着我们的水色的人所见到的是黑的,或深棕色的,一个到河水中游泳的人,河水像所有的湖一样,会给他染上一种黄颜色;但是这个湖水却是这样地纯洁,游泳者会白得像大理石一样,而更奇怪的是,在这水中四肢给放大了,并且给扭曲了,形态非常夸张,值得让米开朗琪罗来作一番研究。水是这样的透明,二十五至三十英尺下面的水底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赤脚踏水时,你看到在水面下许多英尺的地方有成群的鲈鱼和银鱼,大约只一英寸长,连前者的横行的花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你会觉得这种鱼也是不愿意沾染红尘,才到这里来生存的。
有一次,在冬天里,好几年前了,为了钓梭鱼,我在冰上挖了几个洞,上岸之后,我把一柄斧头扔在冰上,可是好像有什么恶鬼故意要开玩笑似的,斧头在冰上滑过了四五杆远,刚好从一个窟窿中滑了下去,那里的水深二十五英尺,为了好奇,我躺在冰上,从那窟窿里望,我看到了那柄斧头,它偏在一边头向下直立着,那斧柄笔直向上,顺着湖水的脉动摇摇摆摆,要不是我后来又把它吊了起来,它可能就会这样直立下去,直到木柄烂掉为止。
就在它的上面,用我带来的凿冰的凿子,我又凿了一个洞,又用我的刀,割下了我看到的附近最长的一条赤杨树枝,我做了一个活结的绳圈,放在树枝的一头,小心地放下去,用它套住了斧柄凸出的地方,然后用赤杨枝旁边的绳子一拉,这样就把那柄斧头吊了起来。湖岸是由一长溜像铺路石那样的光滑的圆圆的白石组成的;除一两处小小的沙滩之外,它陡立着,纵身一跃便可以跳到一个人深的水中;要不是水波明净得出奇,你决不可能看到这个湖的底部,除非是它又在对岸升起。有人认为它深得没有底。它没有一处是泥泞的,偶尔观察的过客或许还会说,它里面连水草也没有一根;至于可以见到的水草,除了最近给上涨了的水淹没的、并不属于这个湖的草地以外,便是细心地查看也确实是看不到菖蒲和芦苇的,甚至没有水莲花,无论是黄色的或是白色的,最多只有一些心形叶子和河蓼草,也许还有一两张眼子菜;然而,游泳者也看不到它们;便是这些水草,也像它们生长在里面的水一样的明亮而无垢。岸石伸展入水,只一二杆远,水底已是纯粹的细沙,除了最深的部分,那里总不免有一点沉积物,也许是腐朽了的叶子,多少个秋天来,落叶被刮到湖上,另外还有一些光亮的绿色水苔,甚至在深冬时令拔起铁锚来的时候,它们也会跟着被拔上来的。
我们还有另一个这样的湖,在九亩角那里的白湖,在偏西两英里半之处;可是以这里为中心的十二英里半径的圆周之内,虽然还有许多的湖沼是我熟悉的,我却找不出第三个湖有这样的纯洁得如同井水的特性。大约历来的民族都饮用过这湖水,艳羡过它并测量过它的深度,而后他们一个个消逝了,湖水却依然澄清,发出绿色。一个春天也没有变化过!也许远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时,那个春晨之前,已经存在了,甚至在那个时候,随着轻雾和一阵阵的南风,飘下了一阵柔和的春雨,湖面不再平静了,成群的野鸭和天鹅在湖上游着,它们一点都没有知道逐出乐园这一回事,能有这样纯粹的湖水真够满足啦。就是在那时候,它已经又涨,又落,纯清了它的水,还染上了现在它所有的色泽,还专有了这一片天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它是天上露珠的蒸馏器。谁知道,在多少篇再没人记得的民族诗篇中,这个湖曾被誉为喀斯泰里亚之泉?在黄金时代里,有多少山林水泽的精灵曾在这里居住?这是在康科德的冠冕上的第一滴水明珠。
第一个到这个湖边来的人们可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我曾经很惊异地发现,就在沿湖被砍伐了的一个浓密的森林那儿,峻削的山崖中,有一条绕湖一匝的狭窄的高架的小径,一会儿上,一忽儿下,一会儿接近湖,一忽儿又离远了一些,它或许和人类同年,土著的猎者,用脚步走出了这条路来,以后世世代代都有这片土地上的居住者不知不觉地用脚走过去。冬天,站在湖中央,看起来这就更加清楚,特别在下了一阵小雪之后,它就成了连绵起伏的一条白线,败草和枯枝都不能够掩蔽它,许多地点,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看起来还格外清楚,但是夏天里,便是走近去看,也还是看不出来。
可以说,雪花用清楚的白色的浮雕又把它印刷出来了。但愿到了将来,人们在这里建造一些别墅的装饰庭园时,还能保留这一残迹。湖水时涨时落,但是有没有规律,如有规律,又是怎样的周期,谁也不知道,虽然有不少人,照常要装作是知道的。冬天的水位通常要高一些,夏天的总低一些,但水位与天气的干燥潮湿却没有关系。我还记得,何时水退到比我住在那儿的时候低了一两英尺,何时又涨高了至少有五英尺。有一个狭长的沙洲伸展到湖中,它的一面是深水,离主岸约六杆,那大约是一八二四年,我曾在上面煮开过一壶杂烩,可是一连二十五年水淹没了它,我无法再去煮什么了;另一方面,当我告诉我的朋友们说,数年之后,我会经常垂钧在森林中的那个僻隐的山凹里,驾一叶扁舟,在离开他们现在看得见的湖岸约十五杆的地方,那里早已成为一片草地了,他们常常听得将信将疑。可是,两年来,湖一直在涨高,现在,一八五二年的夏天,比我居住那儿的时候已经高出五英尺,相当于三十年之前的高度,在那片草地上又可以垂钓了。
从外表看,水位已涨了六七英尺,但是从周围的山上流下来的水量实际上不多,涨水一定是由于影响它深处泉源的一些原因。同一个夏天里水又退了。惊人的是这种涨落,不管它有否周期,却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完成。我观察到一次涨,又部分地观察了两次退,我想在十二或十五年后,水位又要降落到我以前知道的地方。偏东一英里,茀灵特湖有泉水流入,又流水出去,是激荡涨落的,而一些介乎中间的较小的湖沼却和同进退,最近也涨到了它们的最高的水位,时间与后者相同。根据我的观察所及,白湖的情形也如此。间隔很久的瓦尔登湖的涨落至少有这样一个作用:在最高的水位维持了一年左右,沿湖步行固然困难了,但自从上一次水涨以来,沿湖生长的灌木和苍松,白桦,桤木,白杨等树木都给冲刷掉了,等它水位退下,就留下一片干净的湖岸,它不像别的湖沼和每天水位涨落的河流,它在水位最低时,湖岸上反而最清洁。
在我屋边的那湖岸上,一排十五英尺高的苍松给冲刷了,仿佛给杠杆掀倒了似的,这样制止了它们的侵占;那树木的大小恰好说明了上次水位上涨到这个高度迄今有了多少年。用这样的涨落方式,湖保持了它的拥有湖岸的权利,湖岸这样被刮去了胡须,树木不能凭着所有权来占领它。湖的舌头舔着,使胡子生长不出来。它时时要舔舔它的面颊。当湖水涨得最高时,桤木,柳树和枫树从它们的淹在水里的根上伸出来大量纤维质的红根须,长达数英尺,离地有三四英尺高,想这样来保护它们自己;我还发现了,那些在岸边高处的浆果,通常是不结果实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就有了丰收。湖岸怎么会铺砌得这样整齐,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乡镇上的人都听到过传说,最年老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在青年时代听来的在古时候,正当印第安人在一个小山上举行狂欢庆典,小山忽然高高升到天上,就像湖现在这样深深降人地下,据说他们做了许多不敬神的行为,其实印第安人从没有犯过这种罪,正当他们这样亵读神明的时候,山岳震撼,大地突然间沉下去,只留下了一个印第安女子,名叫瓦尔登,她逃掉了性命,从此这湖沿用了她的名字。
据揣想是在山岳震撼时,这些圆石滚了下来,铺成了现在的湖岸。无论如何,这一点可以确定,以前这里没有湖,现在却有了一个;这一个印第安神话跟我前面说起过的那一位古代的居民是毫无抵触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初来时,带来一根魔杖,他看到草地上升起了一种稀薄的雾气,那根榛木杖就一直指向下面,直到后来他决定挖一口井。至于那些石子呢,很多人认为它们不可能起固于山的波动;据我观察,四周的山上有很多这样的石子,因此人们不能不在铁路经过的最靠近那湖的地方在两边筑起墙垣;而且湖岸愈是陡削的地方,石子愈是多;所以,不幸的是,这对于我不再有什么神秘了。我猜出了铺砌的人来了。如果这个湖名不是由当地一个叫萨福隆·瓦尔登的英国人的名字化出来的后,那末,我想原来的名字可能是围而得湖。湖对于我,是一口挖好的现成的井。一年有四个月水是冰冷的,正如它一年四季的水是纯净的;我想,这时候它就算不是乡镇上最好的水,至少比得上任何地方的水。在冬天里,暴露在空气中的水,总比那些保暖的泉水和井水来得更冷。
从下午五点直到第二天,一八四六年三月六日正午,在我静坐的房间内,寒暑表温度时而是华氏六十五度,时而是七十度,一部分是因为太阳曾照在我的屋脊上,而从湖中汲取的水,放在这房子里,温度只四十二度,比起村中最冷的一口井里当场汲取的井水还低了一度。
同一天内,沸泉温度是四十五度,那是经我测量的各种水中最最温暖的了,虽然到了夏天,它又是最最寒冷的水,那是指浮在上面的浅浅一层停滞的水并没有混杂在内。在夏天里,因为很深,所以也不同于一般暴露在阳光底下的水。它没有它们那么热。在最热的气候里,我时常汲一桶水,放在地窖里面。它夜间一冷却下来,就整天都冷,有时我也到附近一个泉水里去汲水。过了一个星期,水还像汲出来的当天一样好,并且没有抽水机的味道。谁要在夏天,到湖边去露营,只要在营帐的阴处,把一桶水埋下几英尺深,他就可以不用奢侈的藏冰了。在瓦尔登湖中,捉到过梭鱼,有一条重七磅,且不去说那另外的一条,用非常的速度把一卷钓丝拉走了,渔夫因为没有看到它,估计它稳稳当当有八磅的重量,此外,还捉到过鲈鱼,鳘鱼,有些重两磅,还有银鱼,鳊鱼(学名Leueiscus Pulchellus),极少量的鲤鱼,两条鳗鱼,有一条有四磅重,我对于鱼的重量写得这样详细,因为它们的价值一般是根据重量来决定的,至于鳗鱼,除了这两条我就没有听说过另外的,此外,我还隐约记得一条五英寸长的小鱼,两侧是银色的,背脊却呈青色,性质上近于鲦鱼,我提起这条鱼,主要是为了把事实和寓言连接起来。总之是,这个湖里,鱼并不多。梭鱼也不很多,但它夸耀的是梭鱼。有一次我躺卧在冰上面,至少看到了三种不同的梭鱼,一种扁而长的,钢灰色,像一般从河里捉起来的一样;一种是金晃晃的,有绿色的闪光,在很深的深水中;最后一种金色的,形态跟上一种相近,但身体两侧有棕黑色或黑色斑点,中间还夹着一些淡淡的血红色斑点,很像鲑鱼。
但学名reticulatus(网形)用不上,被称为guttatus(斑斓)才对。这些都是很结实的鱼,重量比外貌上看来要重得多。银鱼、鳘鱼,还有鲈鱼,所有在这个湖中的水族,确实都比一般的河流和多数的别的湖沼中的鱼类,来得更清洁,更漂亮,更结实,因为这里的湖水更纯洁,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区别出来。也许有许多鱼学家可以用它们来培育出一些新品种。此外还有清洁的青蛙和乌龟,少数的淡菜;麝香鼠和貂鼠也留下过它们的足迹;偶尔还有从烂泥中钻出来旅行经过的甲鱼。有一次,当我在黎明中把我的船推离湖岸时,有一只夜里躲在船底下的大甲鱼给我惊拢得不安了。春秋两季,鸭和天鹅常来,白肚皮的燕子(学名Hirundo bicolor)在水波上掠过,还有些身有斑点的田凫(学名Totanus macularius)整个夏天摇摇摆摆地走在石头湖岸上。我有时还惊起了湖水上面、坐在白松枝头的一只鱼鹰;我却不知道有没有海鸥飞到这里来过,像它们曾飞到过美港去那样。至多每年还有一次潜水鸟要来。常到这里来的飞禽,已全部包罗在内了。在宁静的气候中,坐在船上,你可以看到,东边的沙滩附近,水深八英尺或十英尺的地方,在湖的另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到的,有圆形的一堆堆东西,约一英尺高,直径约六英尺,堆的是比鸡蛋略小的一些圆石,而在这一堆堆圆石周围,全是黄沙。
起初,你会觉得惊奇,是否那些印第安人故意在冰上堆积这些圆石,等到冰溶化了,它们就沉到了湖底;但是,就算这样吧,那形式还是太规则化了,而且有些圆石,显然又太新鲜。它们和河流中可以看见的很相似。但这里没有胭脂鱼或八目鳗,我不知道它是哪一些鱼建筑起来的。也许它是银鱼的巢。这样,水底更有了一种愉快的神秘感了。湖岸极不规则,所以一点不单调。我闭目也能看见,西岸有深深的锯齿形的湾,北岸较开朗,而那美丽的,扇贝形的南岸,一个个岬角相互地交叠着,使人想起岬角之间一定还有人迹未到的小海湾。在群山之中,小湖中央,望着水边直立而起的那些山上的森林,这些森林不能再有更好的背景,也不能更美丽了,因为森林已经反映在湖水中,这不仅是形成了最美的前景,而且那弯弯曲曲的湖岸,恰又给它做了最自然又最愉悦的边界线。不像斧头砍伐出一个林中空地,或者露出了一片开垦了的田地的那种地方,这儿没有不美的或者不完整的感觉。树木都有充分的余地在水边扩展,每一棵树都向了这个方向伸出最强有力的桠枝。大自然编织了一幅很自然的织锦,眼睛可以从沿岸最低的矮树渐渐地望上去,望到最高的树。这里看不到多少人类的双手留下的痕迹。水洗湖岸,正如一千年前。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
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站在湖东端的平坦的沙滩上,在一个平静的九月下午,薄雾使对岸的岸线看不甚清楚,那时我了解了所谓“玻璃似的湖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当你倒转了头看湖,它像一条最精细的薄纱张挂在山谷之上,衬着远处的松林而发光,把大气的一层和另外的一层隔开了。你会觉得你可以从它下面走过去,走到对面的山上,而身体还是干的,你觉得掠过水面的燕子很可以停在水面上。是的,有时它们氽水到水平线之下,好像这是偶然的错误,继而恍然大悟。当你向西,望到湖对面去的时候,你不能不用两手来保护你的眼睛,一方面挡开本来的太阳光,同时又挡开映在水中的太阳光;如果,这时你能够在这两种太阳光之间,批判地考察湖面,它正应了那句话,所谓“波平如镜”了,其时只有一些掠水虫,隔开了同等距离,分散在全部的湖面,而由于它们在阳光里发出了最精美的想象得到的闪光来,或许,还会有一只鸭子在整理它自己的羽毛,或许,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只燕子飞掠在水面上,低得碰到了水。还有可能,在远处,有一条鱼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约三四英尺的圆弧来,它跃起时一道闪光,降落入水,又一道闪光,有时,全部的圆弧展露了,银色的圆弧;但这里或那里,有时会漂着一枝蓟草,鱼向它一跃,水上便又激起水涡。
这像是玻璃的溶液,已经冷却,但是还没有凝结,而其中连少数尘垢也还是纯洁而美丽的,像玻璃中的细眼。你还常常可以看到一片更平滑、更黝黑的水,好像有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把它同其余的隔开似的,成了水妖的栅栏,躺在湖面。从山顶下瞰,你可以看到,几乎到处都有跃起的鱼;在这样凝滑的平面上,没有一条梭鱼或银鱼在捕捉一个虫子时,不会破坏全湖的均势的。真是神奇,这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却可以这么精巧地显现,这水族界的谋杀案会暴露出来我站在远远的高处,看到了那水的扩大的圆涡,它们的直径有五六杆长。
甚至你还可以看到水蝎(学名Gyrinus)不停地在平滑的水面滑了四分之一英里;它们微微地犁出了水上的皱纹来,分出两条界线,其间有着很明显的漪澜;而掠水虫在水面上滑来滑去却不留下显明的可见痕迹。在湖水激荡的时候,便看不到掠水虫和水蝎了,显然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们才从它们的港埠出发,探险似地从湖岸的一面,用短距离的滑行,滑上前去,滑上前去,直到它们滑过全湖。这是何等愉快的事啊。秋天里,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天气中,充分地享受了太阳的温暖,在这样的高处坐在一个树桩上,湖的全景尽收眼底,细看那圆圆的水涡,那些圆涡一刻不停地刻印在天空和树木的倒影中间的水面上,要不是有这些水涡,水面是看不到的。在这样广大的一片水面上,并没有一点儿扰动,就有一点儿,也立刻柔和地复归于平静而消失了,好像在水边装一瓶子水,那些颤栗的水波流回到岸边之后,立刻又平滑了。一条鱼跳跃起来,一个虫子掉落到湖上,都这样用圆涡,用美丽的线条来表达,仿佛那是泉源中的经常的喷涌,它的生命的轻柔的搏动,它的胸膛的呼吸起伏。那是欢乐的震抖,还是痛苦的颤栗,都无从分辨。
湖的现象是何等的和平啊!人类的工作又像在春天里一样的发光了。是啊,每一树叶、桠枝、石子和蜘蛛网在下午茶时又在发光,跟它们在春天的早晨承露以后一样。每一支划桨的或每一只虫子的动作都能发出一道闪光来,而一声桨响,又能引出何等的甜蜜的回音来啊!有时我徜徉到松树密林下,它们很像高峙的庙字,又像海上装备齐全的舰队,树枝像波浪般摇曳起伏,还像涟漪般闪烁生光,看到这样柔和而碧绿的浓荫,便是德罗依德也要放弃他的橡树林而跑到它们下面来顶礼膜拜了,有时我跑到了茀灵特湖边的杉木林下,那些参天大树上长满灰白色浆果,它们越来越高,便是移植到伐尔哈拉去都毫无愧色,而杜松的盘绕的藤蔓,累累结着果实,铺在地上;有时,我还跑到沼泽地区去,那里的松萝地衣像花彩一样从云杉上垂悬下来,还有一些菌子,它们是沼泽诸神的圆桌,摆设在地面,更加美丽的香蕈像蝴蝶或贝壳点缀在树根;在那里淡红的石竹和山茱萸生长着,红红的桤果像妖精的眼睛似地闪亮,蜡蜂在攀援时,最坚硬的树上也刻下了深槽而破坏了它们,野冬青的浆果美得更使人看了流连忘返;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野生的不知名的禁果将使他目眩五色,它们太美了,不是人类应该尝味的。
我并没有去访问哪个学者,我访问了一棵棵树,访问了在附近一带也是稀有的林木,它们或远远地耸立在牧场的中央,或长在森林、沼泽的深处,或在小山的顶上;譬如黑桦木,我就看到一些好标本,直径有两英尺:还有它们的表亲黄桦木,宽弛地穿着金袍,像前述的那种一样地散发香味,又如山毛榉,有这样清洁的树干,美丽地绘着苔藓之色,处处美妙呵,除了一些散在各地的样本,在这乡镇一带,我只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林子,树身已相当大了,据说还是一些被附近山毛榉的果实吸引来的鸽子播下的种子;当你劈开树木的时候,银色的细粒闪闪发光,真值得鉴赏;还有,椴树,角树;还有学名为Celtis occidentalis的假榆树,那就只有一棵是长得好的;还有,可以作挺拔的桅杆用的高高的松树,以及作木瓦用的树;还有比一般松树更美妙的我们的铁杉,像一座宝塔一样矗立在森林中;还有我能提出的许多别的树。在夏天和冬天,我便访问这些神庙。有一次巧极了,我就站在一条彩虹的桥墩上,这条虹罩在大气的下层,给周围的草叶都染上了颜色,使我眼花缭乱,好像我在透视一个彩色的晶体。
这里成了一个虹光的湖沼,片刻之间,我生活得像一只海豚。要是它维持得更长久一些,那色彩也许就永远染在我的事业与生命上了。而当我在铁路堤道上行走的时候,我常常惊奇地看到我的影子周围,有一个光轮,不免自以为也是一个上帝的选民了。有一个访客告诉我,他前面的那些爱尔兰人的影子周围并没有这种光轮,只有土生的人才有这特殊的标识。班文钮托·切利尼在他的回忆录中告诉过我们,当他被禁闭在圣安琪罗宫堡中的时候,在他有了一个可怕的梦或幻景之后,就见一个光亮的圆轮罩在他自己的影子的头上了,不论是黎明或黄昏,不论他是在意大利或法兰西;尤其在草上有露珠的时候,那光轮更清楚。这大约跟我说起的是同样的现象,它在早晨显得特别清楚,但在其余的时间,甚至在月光底下,也可以看到。虽然经常都如此,却从没有被注意,对切利尼那样想象力丰富的人,这就足以构成迷信的基础了。他还说,他只肯指点给少数人看,可是,知道自己有着这种光轮的人,难道真的是卓越的吗? 有一个下午我穿过森林到美港去钓鱼,以弥补我的蔬菜的不足。我沿路经过了快乐草地,它是和倍克田庄紧相连的,有个诗人曾经歌唱过这僻隐的地方,这样开头:“入口是愉快的田野, 那里有些生苔的果树, 让出一泓红红的清溪, 水边有闪逃的麝香鼠, 还有水银似的鳟鱼啊, 游来游去。”还在我没有住到瓦尔登之前,我曾想过去那里生活。
我曾去“钩”过苹果,纵身跃过那道溪,吓唬过麝香鼠和鳟鱼。在那些个显得漫长、可以发生许多事情的下午中间的一个,当我想到该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大自然的生活,因而出动之时,这个下午已过去了一半。还在途中呢,就下了阵雨,使我不得不在一棵松树下躲了半个小时,我在头顶上面,搭了一些树枝,再用手帕当我的遮盖;后来我索性下了水,水深及腰,我在梭鱼草上垂下了钓丝,突然发现我自己已在一块乌云底下,雷霆已开始沉重地擂响,我除了听他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想,天上的诸神真神气,要用这些叉形的闪光来迫害我这个可怜的没有武装的渔人,我赶紧奔到最近一个茅屋中去躲,那里离开无论哪一条路,都是半英里,它倒是跟湖来得近些,很久以来就没有人在那里住了:“这里是诗人所建, 在他的风烛残年, 看这小小的木屋, 也有毁灭的危险。”缪斯女神如此寓言。可是我看到那儿现在住着一个爱尔兰人,叫约翰·斐尔德,还有他的妻子和好几个孩子,大孩子有个宽阔的脸庞,已经在帮他父亲做工了,这会儿他也从沼泽中奔回家来躲雨,小的婴孩满脸皱纹,像先知一样,有个圆锥形的脑袋,坐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像坐在贵族的宫廷中,从他那个又潮湿又饥饿的家里好奇地望着陌生人,这自然是一个婴孩的权利,他却不知道自己是贵族世家的最后一代,他是世界的希望,世界注目的中心,并不是什么约翰·斐尔德的可怜的、饥饿的小子。
我们一起坐在最不漏水的那部分屋顶下,而外面却是大雨又加大雷,我从前就在这里坐过多少次了,那时载了他们这一家而飘洋过海到美国来的那条船还没有造好呢。这个约翰·斐尔德显然是一个老实、勤恳,可是没有办法的人;他的妻子呢,她也是有毅力的,一连不断地在高高的炉子那儿做饭;圆圆的、油腻的脸,露出了胸,还在梦想有一天要过好日子呢,手中从来不放下拖把,可是没有一处看得到它发生了作用。小鸡也躲雨躲进了屋,在屋子里像家人一样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跟人类太相似了,我想它们是烤起来也不会好吃的。它们站着,望着我的眼睛,故意来啄我的鞋子。同时,我的主人把他的身世告诉了我,他如何给邻近一个农夫艰苦地在沼泽上工作,如何用铲子或沼泽地上用的锄头翻一片草地,报酬是每英亩十元,并且利用土地和肥料一年,而他那个个子矮小、有宽阔的脸庞的大孩子就在父亲身边愉快地工作,并不知道他父亲接洽的是何等恶劣的交易。
我想用我的经验来帮助他,告诉他我们是近邻,我呢,是来这儿钓鱼的,看外表,好比是一个流浪人,但也跟他一样,是个自食其力的人;还告诉他我住在一座很小的、光亮的、干净的屋子里,那造价可并不比他租用这种破房子一年的租费大;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能够在一两个月之内,给他自己造起一座皇宫来;我是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吃牛油,不喝牛奶,也不吃鲜肉的,因此我不必为了要得到它们而工作;而因为我不拼命工作,我也就不必拼命吃,所以我的伙食费数目很小;可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要茶、咖啡、牛油、牛奶和牛肉,他就不得不拼命工作来偿付这一笔支出,他越拼命地工作,就越要吃得多,以弥补他身体上的消耗,结果开支越来越大,而那开支之大确实比那时日之长更加厉害了,因为他不能满足,一生就这样消耗在里面了,然而他还认为,到美国来是一件大好事,在这里你每天可以吃到茶,咖啡和肉。可是那唯一的真正的美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可以自由地过一种生活,没有这些食物也能过得好,在这个国土上,并不需要强迫你支持奴隶制度,不需要你来供养一场战争,也不需要你付一笔间接或直接的因为这一类事情而付的额外费用。我特意这样跟他说,把他当成一个哲学家,或者当他是希望做一个哲学家的人。
我很愿意让这片草原荒芜下去,如果是因为人类开始要赎罪,而后才有这样的结局的。一个人不必去读了历史,才明白什么东西对他自己的文化最有益。可是,唉!一个爱尔兰人的文化竟是用一柄沼泽地带用的锄头似的观念来开发的事业。我告诉他,既然在沼泽上拼命做苦工,他必须有厚靴子和牢固衣服,它们很快就磨损破烂了,我却只穿薄底鞋和薄衣服,价值还不到他的一半,在他看来我倒是穿得衣冠楚楚,像一个绅士(事实上,却并不是那样),而我可以不花什么力气,像消遣那样用一两小时的时间,如果我高兴的话,捕捉够吃一两天的鱼,或者赚下够我一星期花费的钱。如果他和他的家庭可以简单地生活,他们可以在夏天,都去拣拾越橘,以此为乐。
听到这话,约翰就长叹一声,他的妻子两手叉腰瞪着我,似乎他们都在考虑,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始过这样的生活,或者学到的算术是不是够他们把这种生活坚持到底。在他们看来,那是依靠测程和推算,也不清楚这样怎么可以到达他们的港岸;于是我揣想到了,他们还是会勇敢地用他们自己的那个方式来生活,面对生活,竭力奋斗,却没法用任何精锐的楔子楔入生活的大柱子,裂开它,细细地雕刻;他们想到刻苦地对付生活,像人们对付那多刺的蓟草一样。
可是他们是在非常恶劣的形势下面战斗的,唉,约翰·斐尔德啊!不用算术而生活,你已经一败涂地了。“你钓过鱼吗?”我问。“啊,钓过,有时我休息的时候,在湖边钓过一点,我钓到过很好的鲈鱼。”.你用什么钓饵!”“我用鱼虫钓银鱼,又用银鱼为饵钓鲈鱼。”“你现在可以去了,约翰,”他的妻子容光焕发、满怀希望他说;可是约翰踌躇着。阵雨已经过去了,东面的林上一道长虹,保证有个美好的黄昏;我就起身告辞。出门以后,我又向他们要一杯水喝,希望看一看他们这口井的底奥,完成我这一番调查;可是,唉!井是浅的,尽是流沙,绳子是断的,桶子破得没法修了。这期间,他们把一只厨房用的杯子找了出来,水似乎蒸馏过,几经磋商,拖延再三,最后杯子递到口渴的人的手上,还没凉下来,而且又混浊不堪。我想,是这样的脏水在支持这几条生命;于是,我就很巧妙地把灰尘摇到一旁,闭上眼睛,为了那真诚的好客而干杯,畅饮一番。在牵涉到礼貌问题的时候,我在这类事情上,并不苛求。
雨后,当我离开了爱尔兰人的屋子,又跨步到湖边,涉水经过草原上的积水的泥坑和沼泽区的窟窿,经过荒凉的旷野,忽然有一阵子我觉得我急于去捕捉梭鱼的这种心情,对于我这个上过中学、进过大学的人,未免太猥琐了;可是我下了山,向着满天红霞的西方跑,一条长虹挑在我的肩上,微弱的铃声经过了明澈的空气传入我的耳中,我又似乎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我的守护神在对我说话了,要天天都远远地出去渔猎,越远越好,地域越宽广越好,你就在许多的溪边,许许多多人家的炉边休息,根本不用担心。记住你年轻时候的创造力。黎明之前你就无忧无虑地起来,出发探险去。让正午看到你在另一个湖边。夜来时,到处为家。没有比这里更广大的土地了,也没有比这样做更有价值的游戏了。按照你的天性而狂放地生活,好比那芦苇和羊齿,它们是永远不会变成英吉利干草的啊。
让雷霆咆哮,对稼穑有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并不是给你的信息。他们要躲在车下,木屋下,你可以躲在云下。你不要再以手艺为生,应该以游戏为生。只管欣赏大地,可不要想去占有。由于缺少进取心和信心,人们在买进卖出,奴隶一样过着生活哪。呵,倍克田庄!以小小烂漫的阳光 为最富丽的大地风光。牧场上围起了栏杆, 没有人会跑去狂欢。你不曾跟人辩论, 也从未为你的疑问所困, 初见时就这样驯良, 你穿着普通的褐色斜纹。爱者来, 憎者亦来, 圣鸽之子, 和州里的戈艾〃福克斯, 把阴谋吊在牢固的树枝上! 人们总是夜来驯服地从隔壁的田地或街上,回到家里,他们的家里响着平凡的回音,他们的生命,消蚀于忧愁,因为他们一再呼吸着自己吐出的呼吸;早晨和傍晚,他们的影子比他们每天的脚步到了更远的地方。我们应该从远方,从奇遇、危险和每天的新发现中,带着新经验,新性格而回家来。我还没有到湖边,约翰·斐尔德已在新的冲动下,跑到了湖边,他的思路变了,今天日落以前不再去沼泽工作了。
可是他,可怜的人,只钓到一两条鱼,我却钓了一长串,他说这是他的命运;可是,后来我们换了座位,命运也跟着换了位。可怜的约翰·斐尔德!我想他是不会读这一段话的,除非他读了会有进步,他想在这原始性的新土地上用传统的老方法来生活,用银鱼来钓鲈鱼。
有时,我承认,这是好钓饵。他的地平线完全属于他所有,他却是一个穷人,生来就穷,继承了他那爱尔兰的贫困或者贫困生活,还继承了亚当的老祖母的泥泞的生活方式,他或是他的后裔在这世界上都不能上升,除非他们的长了蹼的陷在泥沼中的脚,穿上了有翼的靴。

点击 阅读原文 完成今日签到打卡